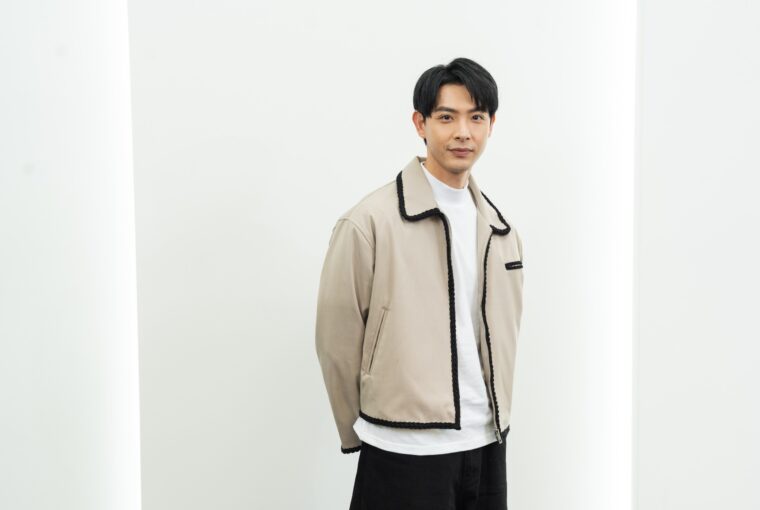大概是晚上八點左右的時間,張孝全坐在一個地鐵站的長椅上,某班列車駛進月台,一群人陸陸續續地從車廂裡走出,有些是晚下班的上班族,有些是補完習的學生。他看著這樣的情景,坐著抽菸,不疾不徐地抽著,一吸,又一吐,然後就這樣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等到一根菸抽完(也有可能不只一根),他捻熄了菸蒂,好像有什麼東西已經被滿足了,起身準備回家。
這是張孝全想像此刻所處的一種精神狀態,似乎很放鬆,卻又帶著某種輕微地焦慮,「過去你改變不了,那可能真的有影響到你,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但現在你自知你身邊有一群很好的人,會告訴你一些問題,給你一些建議,如果你願意接受的話,那些東西的改變,就是關乎你的未來。」高中就出道的他,因為想買車,誤打誤撞開始了演員之路,就這樣演了二十多個年頭。但他從不把時間軸拉遠,設定自己想成為的某種樣子,因為對他而言,未來隨時會改變,人生最有趣的就是這種「未知」。
-683x1024.jpg)
-683x1024.jpg)
演員要百分之百變成另外一個人,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這樣的未知對張孝全來說是那麼令人興奮,即便已在破百個角色中流轉,他仍然享受這樣的感覺,「如果你對這個角色或故事有熱情,那就是天助我也;那如果你發現自己沒有熱情,但你還是必須做下去,那就是你必須當下去面對解決;但有時候也有可能是你覺得很有興趣,很有熱情,但最後你卻把他搞砸了;最後也有可能是你覺得好痛苦,快要不行了,但你最後得到的卻是最多的。」他認為,人的狀態會隨著時間不斷的改變,不會有一定的答案。他回憶起以前曾因為職業倦怠跑去當兵,也曾演到一半任性休息了一年,但現在這套方法對他而言,可能也不見得管用,永遠都可以發現自己新的改變和新的想法。


對「未知」的接納和開放,也反映在張孝全準備角色功課的狀態。年輕的時候他靠直覺,後來他發現讓角色增加厚度的方法,就是需要去用力分析和理解,進入故事的核心,但近來他反而會問自己,一個角色真的只有一個方法嗎?有哪一個理解方式是絕對正確的嗎?「我覺得有時候這是一種『取捨』,你應該讓他在那個當下發生,因為對角色來說,重頭戲有可能就是接下來要發生的事。」他說,演員做角色功課絕對是件好的事,但很多時候功課做完,最需要的反而是把角色功課丟掉,不然會容易覺得一切都不合理,讓自己被困在裡面。
「演戲當然越演會越熟練,但這個熟練到底是不是我需要的?從原本不熟練到熟練花了十年,但接下來突然我不要這個熟練了,要把這十年的東西丟掉很難嗎?很難、超難!」張孝全苦笑著說,作為一個演員,每次聊到這些表演的事情,講了一堆,總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沒有講,但確實每一個角色對他來說,正因為這樣的未知性,他反而覺得答案不重要了。他能做到的,或許也只有盡力拉近每個角色和自己的距離,「但要真的百分之百成為另外一個人,那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成就感來自忘我的瞬間,活在角色的當下會忽略鏡頭
演員要成為另一個人有多難?如果自己的人生跟這個角色有點重疊,或許還能夠有共感;又或許他可以靠著田調訪問,來取樣為演出的能量,但如果你沒有刑求過別人,你也沒有殺過人,離自己的生命經驗超級遙遠宛若平行世界的角色,又該怎麼辦呢?電影《器子》中張孝全飾演的張其茂充滿了暴戾之氣,因為女兒被綁,妻子被逼自殺,他甚至被栽贓誣陷,進了監獄。出獄後,憤怒的他踏上了一段漫長的復仇之路,在抽絲剝繭之下,找出當年參與女兒人口販售的相關人士,一步步的對他認為的那些有罪之人,進行最嚴厲的懲罰。
。-華映娛樂提供.jpg)
。-華映娛樂提供.jpg)
「他的恨是有階段性的,當他自己成為父親的時候,孩子不見了那是第一層;然後他開始尋找孩子,發現其中可能存在著什麼問題,這是第二層;再來是他的太太接受不了自殺了,這是第三層,接下來,他覺得他好像有機會知道什麼,得到了一些線索,開始一層一層的推進。」集中對角色的想像,是張孝全在演戲時候最重要的事情,但這個「想像」有時候沒有辦法靠一個人完成,需要靠導演、燈光、美術、道具、對手演員,是整個環境還有人都要一起幫忙,在最理想的狀況下,大家對於角色的認知要在同一個基準點。
張孝全舉例,最簡單的或許是對一場戲的表達,是要笑還是要哭,但是就連「笑」也都有好幾種區分,「你對笑的想像是『不哭』,這就可能跟我對笑的想像不一樣;也有可能我想像的這個笑是因為真的覺得好笑,但是導演想像的笑是因為他必須藏住這個難過,所以要用笑的方式表達,大家看見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一旦確立了對角色的想像,張孝全就可以完全投入,到達「忘我」的境界。
.jpg)
.jpg)
「你會覺得你活在那個當下,沒有太多思考,沒有太多關於鏡頭、關於角色、關於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那種東西不一定會有,有的時候當然就是很棒的東西。」張孝全分享,演員最大的成就感之一,就是可以在這麼短的一段時間裡,和大家培養出默契。原本可能是一群陌生人,但開拍之後,他可能有了老婆,有了女兒,有了一個家,甚至是劇組人員同樣為了這個「家」而努力,最後將作品呈現到觀眾眼前,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平時會買好料請小球員們共享。華映娛樂提供.jpg)
平時會買好料請小球員們共享。華映娛樂提供.jpg)
不擅長用眼淚表現情緒,哭戲仍是內心最大障礙
然而即便演得忘我,唯有「哭戲」至今仍然是張孝全的心理障礙,「其實我一直不是一個會帶入自己人生經歷的演員,如果有一場哭戲,要我去帶入我的家人,或是曾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會瞬間全世界最清醒。我怎麼會現在我是張其茂,然後又是張孝全因為什麼事情哭得很難過?我反而會跳出來,覺得這一切都是假的。」從小張孝全就不是個愛哭的人,由於太少選擇用哭來表達情緒,有時候他甚至也會跟導演討論,是不是可以用別的方式做表達,如果真的一定需要哭,他會需要更多的時間準備,增加角色的熟悉感,所以要看到他像在《器子》裡和女兒對戲哭得淅瀝嘩啦的場景,可真的是不太容易。
相較於《器子》裡被仇恨吞噬的張其茂,現在的張孝全是幸福的,對於演戲還保持著熱情,家庭也開心美滿,雖然有時候還是有壓力,但處理的方式也和過往完全不同。以前的張孝全熱愛衝浪、拳擊、騎車,但因為把這件情做為宣洩壓力的過程,有時候會不小心太用力,導致身體受傷,「但現在我不需要用這樣的方式燃燒自己,遇到壓力我會想著要如何解決,理性去想他的根源。」愛好就該是做起來開心的事,而不是抵消壓力的手法,對於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張孝全的心態更加餘裕,也更加自然。


「滴答…滴答…滴答…」張孝全模擬著時鐘的音效,眼神透露著一份踏實,「就算你不動,時間也在往前走,你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他也還在那滴答…滴答…滴答…」時間推著他繼續向前,有時候對自己超有自信,有時候又對於挑戰感到緊張,當他翻開人生每一張覆蓋的牌,他的手都會是顫抖的,因為他知道,每一個未知,都會讓他熱血沸騰。
-2-683x1024.jpg)
-2-683x1024.jpg)
採訪撰文/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攝影/坤哥

的工程師直男個性吸引到何百芮(圖右,)但有時也讓她大翻白眼——在戀愛世界裡,情人的優缺點常常是一體兩面的。(圖/彼此影業提供)-110x85.jpg)





-1-760x51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