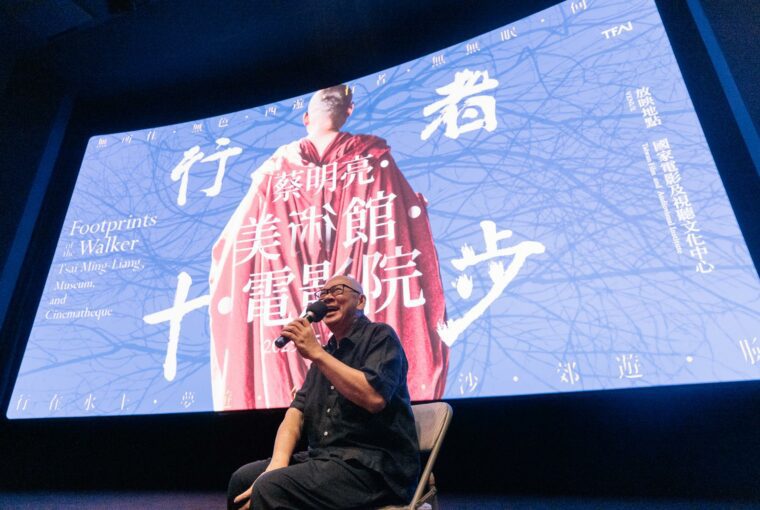由日本名導濱口龍介執導的《在車上》是一部改編自村上春樹收錄在《沒有女人的男人們》小說集中〈Drive My Car〉、〈雪哈拉莎德〉、〈木野〉三篇文章的作品,並由西島秀俊主演。此片自開拍消息傳出即受各界期待,是近年最受國際關注的日本電影之一。
濱口龍介將原著中,關於失落與懷疑的情感肌理,擴展為一部長篇電影,更巧妙揉合契訶夫《凡尼亞舅舅》的劇場演出元素,使原本內省的小說文本,有了跨媒介的延伸與迴響。《在車上》也一舉囊括2021年第74屆坎城影展最佳劇本獎、第79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更是首部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日本電影,並在2022年第94屆奧斯卡金像獎獲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國際影片四項大獎提名,最終斬獲最佳國際影片殊榮。
註解:《凡尼亞舅舅》(Uncle Vanya)是俄羅斯劇作家安東・契夫( Anton Chekhov)創作的一部戲劇,於 1897 年首次出版。該劇講述了一位老教授和他美麗而年輕得多的第二任妻子葉蓮娜前往維持他們城市生活方式的鄉村莊園的故事。
(本文有部分劇情透露,請謹慎點閱)


一段關於失落與重建的旅程
《在車上》是一部關於失語、傾聽與療癒的電影,濱口龍介不急於揭示答案,而是讓觀眾在近三小時的片長中,與角色一同經歷內心的波動與轉折。這是一段在車上展開的心靈旅程,透過靜謐的對話與沉默,逐步揭示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與連結。
主角家福悠介是一位舞台劇導演兼演員,與妻子音的婚姻表面平靜,實則暗藏裂痕,因為太害怕得知真相,不敢戳破妻子偷情,此事也在妻子突然過世後,成為他抑鬱難解的心結。兩年後,家福悠介受邀到廣島指導舞台劇《凡尼亞舅舅》,並被指派一位寡言的年輕女司機美沙紀,在每日的車程中,兩人逐漸打開心扉,彼此分享過往的傷痛與秘密。
電影以緩慢的節奏,細膩描繪角色內心的變化。車內的對話成為情感交流的主要場域,觀眾彷彿與角色一同坐在後座,靜靜聆聽他們的故事。而這樣一段關於喪失與重建的旅程,也說明了,當一個人無法直視創傷,就必須經歷一場繞行的長路。


多語言排練象徵溝通的多重面向
電影中,家福悠介指導的《凡尼亞舅舅》採用多語言演出,包括日語、韓語、英語與手語。這種排練方式看似困難重重,卻象徵著溝通的多重面向。即使語言不同,演員們仍能透過肢體語言與情感表達,達成理解與共鳴。
其中,一位演員以手語表演的場景令人印象深刻,他展現了無聲卻極具力量的情感傳達。濱口龍介在此不僅挑戰舞台表演的形式界限,也讓觀眾重新體認到,溝通從來不只是言語,更是一種對彼此的信任與接納。


紅色薩博汽車中的沈默、共鳴與情感
「車內」的空間在電影中具有特殊意義。它既是封閉的,也是開放的,讓角色在其中感到安全,得以坦露心聲。家福悠介與美沙紀的對話不多,但每一句話都充滿重量,他們談論過去的創傷、對親人的思念,以及對未來的迷惘。
這些對話不僅讓角色彼此理解,也讓觀眾感受到人與人之間微妙的情感連結。甚至可以說,沉默在本片中擁有與語言同等份量。正是在那些欲言又止的空隙中,角色的情感逐漸清晰起來,而觀眾也獲得傾聽的空間。
另外,電影中的紅色薩博(SAAB900)汽車,不僅是交通工具,更是承載記憶與情感的載體。家福悠介與妻子曾在車上共同排練劇本,車內錄音成為他與妻子之間的連結。在妻子過世後,這輛車成為他懷念與思考的空間。
車內的錄音帶播放著妻子的聲音,讓家福悠介在行駛中反覆聆聽,彷彿與妻子對話。這種方式既是對過去的追憶,也是對自我的審視。當過往的聲音與現在的沉默交錯,觀眾也在這趟旅程中看見「喪失」與「記憶」如何共存。
汽車是承載記憶與情感的載體。-1024x576.jpg)
汽車是承載記憶與情感的載體。-1024x576.jpg)
村上村樹作品最成功的一次改編
《在車上》是一部需要細細咀嚼的電影,不過正因它誠實地對待情緒與人性,反而更能跨越文化藩籬,打動來自不同語言背景的觀眾,這也正是它在國際影壇備受矚目的原因。
自2021年於坎城影展首映後,此片即斬獲最佳劇本獎,並在接續的一年間陸續獲得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紐約影評人協會最佳影片、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最佳導演、英國電影學院獎(BAFTA)最佳非英語片、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成為日本近十年來在國際影壇最耀眼的藝術電影之一。
對於村上春樹來說,電影《在車上》不僅是一次成功的改編,也或許是他作品中最具「影像生命」的一次轉譯;而對於濱口龍介來講,這部片既是對劇場語言的深刻反思,也是他導演生涯的轉捩點。《在車上》讓我們相信,哪怕人生看似無解,只要願意傾聽,在沉默與行駛之間,仍有可能聽見愛與救贖的回音。
撰文/張博瑞
責任編輯/張博瑞
核稿編輯/李羏
與桂綸鎂飾演的夫妻,在長年壓抑與失衡中逐漸崩解-110x85.jpg)





與桂綸鎂飾演的夫妻,在長年壓抑與失衡中逐漸崩解-760x510.jpg)

與金馬怪物演員方郁婷(右)在電影《大濛》中飾演兄妹,年紀差8歲的兩人站在一起相當有兄妹氣息。/華文創-提供-760x51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