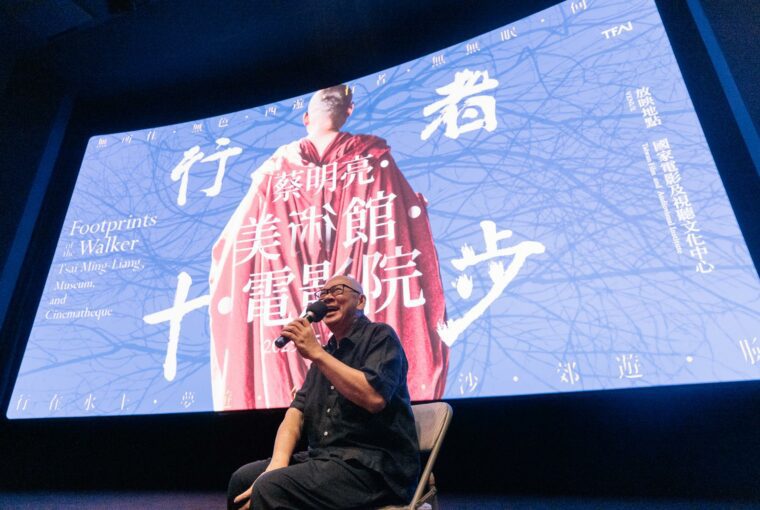亞洲電影在全球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卻少有獎項能全面呈現其產業樣貌。觀察全球以「亞洲」為範圍的電影獎或影展,常見兩個侷限:一是以「亞洲新銳」為主,如釜山影展的招牌單元「新浪潮獎」,專選亞洲新導演第一、二部作品進行競賽,是潛力創作者嶄露頭角的重要舞台,但反而少有機會讓亞洲各地影人,不分資歷與世代同場較量;二是在歐美常見的亞洲電影節,選片人與目標觀眾多是歐美人士,容易帶著外部眼光,也多選藝術片。


而「亞洲電影大獎 (Asian Film Awards, AFA)」,由釜山、香港、東京三個亞洲大型國際電影節共同創立的「亞洲電影大獎學院」運作,2025年邁入第十八屆,是少數為亞洲電影提供全面競技場的權威獎項。一方面涵蓋廣泛地域,不只包含華語區與日韓,還囊括東南亞、中亞、南亞等地,視亞洲為整體;另一方面站在產業內部,品味兼容雅俗。
本屆2025年入圍的五部最佳影片,或可作為當代亞洲電影發展輪廓的觀察指標。
現象級商業大作:《破墓》與《九龍城寨之圍城》
2025年最有票房號召力的入圍影片,當屬韓國靈異片《破墓》與香港動作片《九龍城寨之圍城》。前者是韓國年度票房冠軍,後者在香港締造破億港元佳績;來台亦受歡迎,前者全台破億,後者達四千萬新台幣,展現韓港在台底氣。
韓國影視競爭力無庸置疑,《破墓》站在巨人肩膀上,集結強大卡司與製作資源,完成一次漂亮的類型融合兼創新。故事講述兩名巫覡受託化解富豪的祖墳災厄,聯手風水師與禮儀師組隊破墓。前半是走氣氛的鬼片加上民俗科普,對手是無形怨靈,後半居然超展開,變成與有形怪物的血肉搏殺,甚至牽扯日殖背景。收尾留下伏筆,儼然是另一個韓國影視IP的誕生。


台灣觀眾看《破墓》或許很有既視感,命理禁忌、糯米驅魔、五行相剋、祖墳作祟,讓人想起林正英殭屍片,導演張在現也坦言參考過《暫時停止呼吸》。類型電影本是套路重組,《破墓》雖採韓片常有的「拿來主義」,仍走出獨特格局與氣質。後段轉入怪物片並強打抗日激情,或許會被批評,太有形削弱了恐怖感,太民族主義也讓部分觀眾反感,但作為主流商業片,追求張力與新鮮變奏無可厚非。而韓國影視一向擅長的氛圍營造、明星魅力與娛樂效果,同樣做好做滿很難挑剔,女星金高銀把傳統「跳大神」薩滿儀式跳成讓人目不轉睛的時尚秀,再次展現韓國強勁軟實力。
儘管香港電影啟發了《破墓》,但不過才幾年前,「港產片已死」論調仍甚囂塵上。《九龍城寨之圍城》是從谷底竄出的華麗一舞,也是這波復甦中的一劑強心針。
九龍城寨,已消失的香港城中城,因政治因素成為三不管地帶,群集難民與罪犯。長年下來,人口密度高,黃賭毒猖獗,違建蔓生,通道幽閉錯綜如迷宮。在1994年拆除後,從此成為傳說。電影採實景混搭電腦特效,斥鉅資打造城寨,並充分利用城寨的空間特色,以老派男性義氣為情感核心,在迷宮巷弄中大玩凌厲打鬥與飛簷走壁。導演鄭保瑞本是千禧年後港產動作片旗手,亦在中國神話大片《西遊記之大鬧天宮》掌舵新科技與高成本。本片結合在地關懷與新技術,推至港產動作片新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電影帶有濃厚懷舊風,城寨中的人情味,恍如周星馳電影《功夫》的豬籠城寨翻版。古天樂飾演的城寨大家長,更像守護社區的里長伯,而非冷血黑幫。片尾夕陽柔暉下,城寨如香港縮影,用「離不開,留不下」不如多看幾眼的城市寓言,回應港人當下迷惘。


名導的藝術精進:《狗陣》與《生之敵》
曾以《鬥牛》奪下金馬最佳改編劇本的導演管虎,2024年以《狗陣》在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打敗《喵的奇幻漂流》等國際強片拿下最佳影片。這是管虎至今的國際影展最高榮譽,也是當年中國電影海外參展的最好成績,不意外地成為本屆亞洲電影大獎的中國代表。
故事發生於2008年北京奧運前,有別於彼方首都的高調慶賀,此處是荒蕪的西北大漠,小鎮將拆遷,居民散去徒留成群浪犬,四處遊蕩被當亂源。彭于晏飾演剛出獄的主角,在管虎說法是「趕不上經濟發展快速列車的人」,無法適應外界巨變而失語。他與被認定狂犬病而通緝的黑狗,均不被集體接納,在邊緣相遇,自此相依靠。
全片情節極簡,讓觀眾靜觀跨物種互動,細思背後象徵性。在大量壯觀遠景下,荒涼戈壁成了另一主角,純視聽跨越語言與文化藩籬,或許也是本片在歐美好評如潮的原因之一。嚴肅寓言格局之餘不失幽默,彭于晏默片喜劇般的肢體表演、黑狗小辛的靈動萌態(以本片榮獲坎城影展狗狗金棕櫚獎),均令人莞爾。


日本名導吉田大八,則以《生之敵》再攀頂峰,去年在東京影展橫掃最佳影片、導演與男主角三大獎。這是一部黑白藝術片,本土票房恐怕不會太好,海外影展目前似乎走得並不順,幸好有在亞洲電影大獎入圍六項維持聲勢(東京影展大贏家常能在亞洲電影大獎有所表現)。
這是吉田大八在《聽說桐島退社了》後最好的作品。如果《聽說桐島退社了》透過不停移動的人物視角,帶出人際網絡的土崩瓦解、高中生的存在危機;《生之敵》則以貌似穩固的單一視角、寫實鋪陳與身心狀態,由內而外帶來坍方,並將陷落的自我凝視為深不見底的存在深淵。
本片改編自日本文壇鬼才筒井康隆的小説,講述退休老教授的獨居生活。開場如《我的完美日常》,做菜、起居、工作,建構周而復始的完美秩序;然而日常很快被打亂、遭入侵,有人拜訪,有情慾波瀾,還有神秘的「北方敵人將至」訊息,虛實逐漸模糊,宛如矜持許多、不那麼放飛的暮年版《盜夢偵探》;不知當下是夢還是夢中夢,也似驚悚版的《野草莓》,從垂老視角殘忍回顧自身不堪與死亡恐懼。


筒井康隆的小說經常跳躍時空與虛實,人物趨於概念化,充滿難以用現實邏輯解釋的怪異設定,因此被視為難以影像化。不過一旦找到合適改編策略,往往就是經典,今敏的《盜夢偵探》、細田守的《跳躍吧!時空少女》這兩部動畫皆為成功前例。《生之敵》以真人電影改編,成績同樣斐然,值得更多關注。
印度女性觀點的崛起:《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
觀察今年最佳影片入圍名單,其實多偏男性視角,男性視角不代表作品不好,但作為一份名單,多元性顯有遺憾。因此《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All We Imagine as Light)入圍格外珍貴。
本片不只出自帕亞爾卡帕迪亞(Payal Kapadia)這位印度年輕女導演之手,還是她的首部劇情長片。事實上,包括入圍本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女主角的《警上添花》(Santosh)、在柏林影展引起矚目的《模範生的禁愛祕密》(Girls Will Be Girls),全都是在去年一鳴驚人的印度新銳女導演作品,在父權禁錮、寶萊塢等商業巨片為主的印度,隱隱嗅到異質女力洶湧待發的訊號。
《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去年勇奪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後,挾強勢口碑紅遍全球。故事關於兩名孟買女護士,在父權社會下難以做自己。電影本身沒有太多情節起伏,更多是用飽含詩意與溫柔的紀實鏡頭與配樂,捕捉她們在喧鬧城市的受困狀態,後段再隨角色走入靜謐鄉間,覓得魔幻的喘息片刻。
有趣的是,作為一部性別立場明確的電影,《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並無激進的政治宣言。政治性在片中,恣意流淌為一種純粹的敏銳感性,捕捉個人生命微光、女性情誼的相濡以沫,讓觀者在情感共鳴中自然生出理解與認可。


從靈異、動作、寓言、文學改編到女性敘事,本屆亞洲電影大獎展現亞洲電影在產業與藝術的拓疆野心。這場頂尖對決,無論獎落誰家,都為未來指出新的可能。
文/謝佳錦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