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月老》裡怨念纏身的「厲鬼」鬼頭成,再到影集《愛愛內含光》溫吞內斂的大學教授,這幾年馬志翔持續以多元的角色形象,穿梭於大銀幕、小螢幕中。而電影《獵人兄弟》,則回歸他多年來持續關注的原住民議題 題材,「這部片在某種程度記錄了當下的現況。電影迷人的地方就是這樣,它可以記錄下時代。」
「你怎麼那麼黑?」荒謬刻板印象曾迷惘到排斥自身血統
《獵人兄弟》呈現了原住民文化的傳承與保存、經濟資本對大自然的襲擊,從而帶出原住民身份認同議題。故事以父親(林慶台 飾)的「意外」身亡為引線,引爆林正(馬志翔 飾)與林祥(徐詣帆 飾)兩兄弟的對立面。糾葛難斷的父子關係、兄弟親情的矛盾,實際上皆指向身份認同的內核,「我們都知道文明的碰撞,大的會把小的吃掉,其實最可怕的是,大的把小的同化。」
馬志翔的身份認同旅程,始於二十歲剛入行之時。他幼時長於山上部落,幼稚園時期因父親教育工作搬到山下城鎮,國中到台北唸書,高中則至屏東,大學再回台北。整個求學階段,和故鄉花蓮保持著似遠似近的距離,而同儕與社會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階級假象,讓他漸漸迷失了方向,「你怎麼那麼黑!叫你小黑!」、「你家那邊有路燈嗎?」、「你家有電視嗎?」,一個個荒謬的問題使他越來越困惑,越來越自卑,「我甚至有排斥我自己的血統,不想讓人家知道我是原住民,但明明長得就很像。」


迷失不在於不認同,而是距離產生的隔閡,表演則成了馬志翔打破隔閡的契機。當時鄭文堂執導了「部落三部曲」:《瑪雅的彩虹》、《少年阿霸士》、《瓦旦的酒瓶》,找馬志翔扮演當中的少年阿霸士,戲裡他陪著同為原住民的女主角阿芬回鄉尋根,戲外他也像回了家一樣,「拍攝過程當中就有遇到很多當地的原住民,他們就一直笑我,你原住民這個不懂那個不懂!然後認識了一些大哥,從他們身上我就覺得我是不是要重新去認識自己。」
從原住民古文學開始,馬志翔閱讀了大量的原住民小說、原住民音樂等等,看見了族人面臨的嚴峻問題,了解這些文化正快速地消逝,「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當中,民族自覺是很喜悅的,但相對也很痛苦,因為原來原住民在文化衝擊之下,有很多沒有辦法適應的人,那這些沒有辦法適應的人好像就會變成了家庭問題、教育問題,甚至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沒有人要關心。」


這份喜悅和痛苦,催促他走向了編導創作路。當時雖已是演員,可若沒有人願意寫相關的故事,那他也無從可演,所以怎麼辦?只能自己寫,但寫了誰能有辦法拍出有共鳴的故事,所以不如就自己來拍,「這是我自己在這個行業的歷程,所以當我讀到《獵人兄弟》劇本的時候,其實我是很興奮的,就是原來還是有原住民創作者,有原住民導演,用原住民的嘴巴,說原住民的故事。」


用沒有人要的劇本,拿下第一座金鐘
早些年馬志翔花了不少時間跑台灣原住民部落,從台11線、台9線,再到中橫、北橫、南橫,不敢說全跑完,但能去的都盡量去過。他認為故事沒有所謂的「原創」,所有影像創作皆取自生活,若不知何為生活,就無法說出好故事。
比如2008年,替他拿下第一座金鐘獎最佳迷你劇集導播(演)獎的《說好不准哭》,就是他某次行經花蓮太平部落所獲的靈感。馬志翔回憶,在駛離部落唯一一條道路時,發現路旁有條岔路,岔路裡是所小學,一對兄弟在門口,穿著制服,背著書包,沒有進學校,「我就下車跟他們聊天:『弟弟!幾點了怎麼還在外面!』弟弟就說我爸爸還沒有回來,哥哥就巴他頭說再吵我就揍下去喔!」


馬志翔說得活靈活現,當時的景象依然刻在他腦海,「我就想像這一對兄弟其實是在等爸爸回來,因為他們沒有繳學費不好意思進校門,那爸爸怎麼啦?發生什麼事情?然後我就把它寫成一個故事,金鐘獎就得獎了。」這就是馬志翔找題材的方式。對他來說,題材無法憑空想像,不是坐在電腦前敲打鍵盤就能敲出一座金鐘獎。因為靠想像的故事總是容易流露編撰的影子,經不起推敲。
實際上,馬志翔的第一座金鐘獎,是2007年拿下最佳編劇的《十歲笛娜的願望》。這是他第一部編導作品,也是影響他最深的一部,「它本來是一個沒有人要的劇本。」
他自當兵時開始自學導演功課,退伍後花了兩年的時間寫本,寫了兩個,《十歲笛娜的願望》是其中之一。不斷送案,不斷被退稿,每次被退就一直修,直到某天有個製作人打電話詢問劇本,殊不知一下子兩劇本都被看中。可當時他尚未有導演經驗,所以先找了副導的工作磨練,才稍稍安心地開啟第一次導演旅程,「但是我沒有辦法拍兩部,我只能拍一個,我想要拍那個一直被打槍的劇本。所以我常常跟年輕人分享,不要把逆境當作是不好的事情,別人反對你,你的態度不要掉下去,是不是可以變成你加油的動力?」


每一部創作裡,都有著對已逝父親的嚮往
從《十歲笛娜的願望》、《說好不准哭》再到2014年創造全台破3億票房的《KANO》,馬志翔不只用影像說原住民的故事,也在每部創作中,悄悄埋入關於父親的印記,「父親這一塊,你知道孩子都需要大人的背影跟隨。在我整個成長的過程,甚至於出社會的過程,都沒有一個父親的角色可以依靠、跟隨,或是我不知道該怎麼成為一個父親。」
父親在馬志翔國二時,因一場交通事故逝世。當時人在台北唸書,他形容得知噩耗的狀態,是很不真實的,一滴眼淚都掉不出來,即使回到花蓮,看見躺在冰櫃裡的父親,也沒有任何感覺,一切像夢遊一般。直到三更半夜,突然很想見父親,跑到冰櫃旁朝窗口裡看,「因為會有水氣,我就打開窗,看我爸爸,我看不到我爸爸,因為很暗,它裡面會有燈,我就找開關,找了好久,我是在那個時候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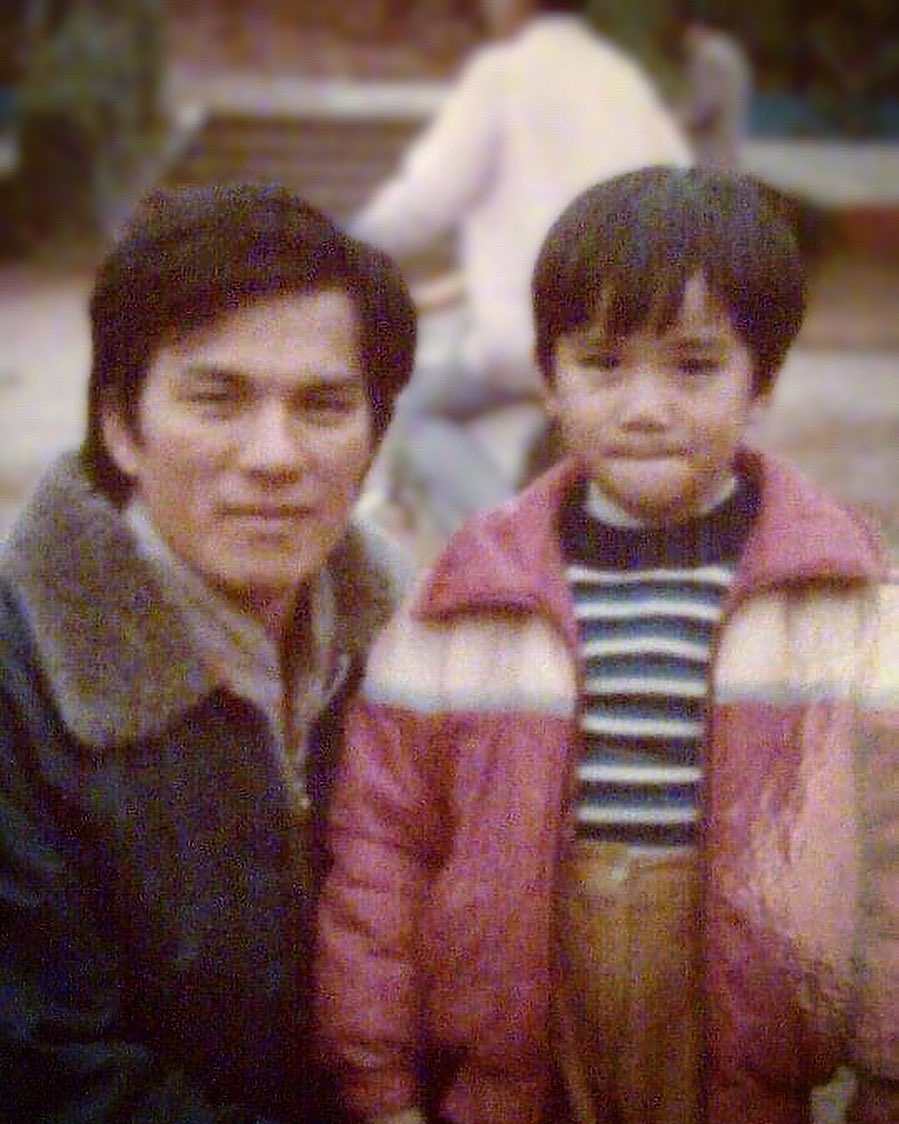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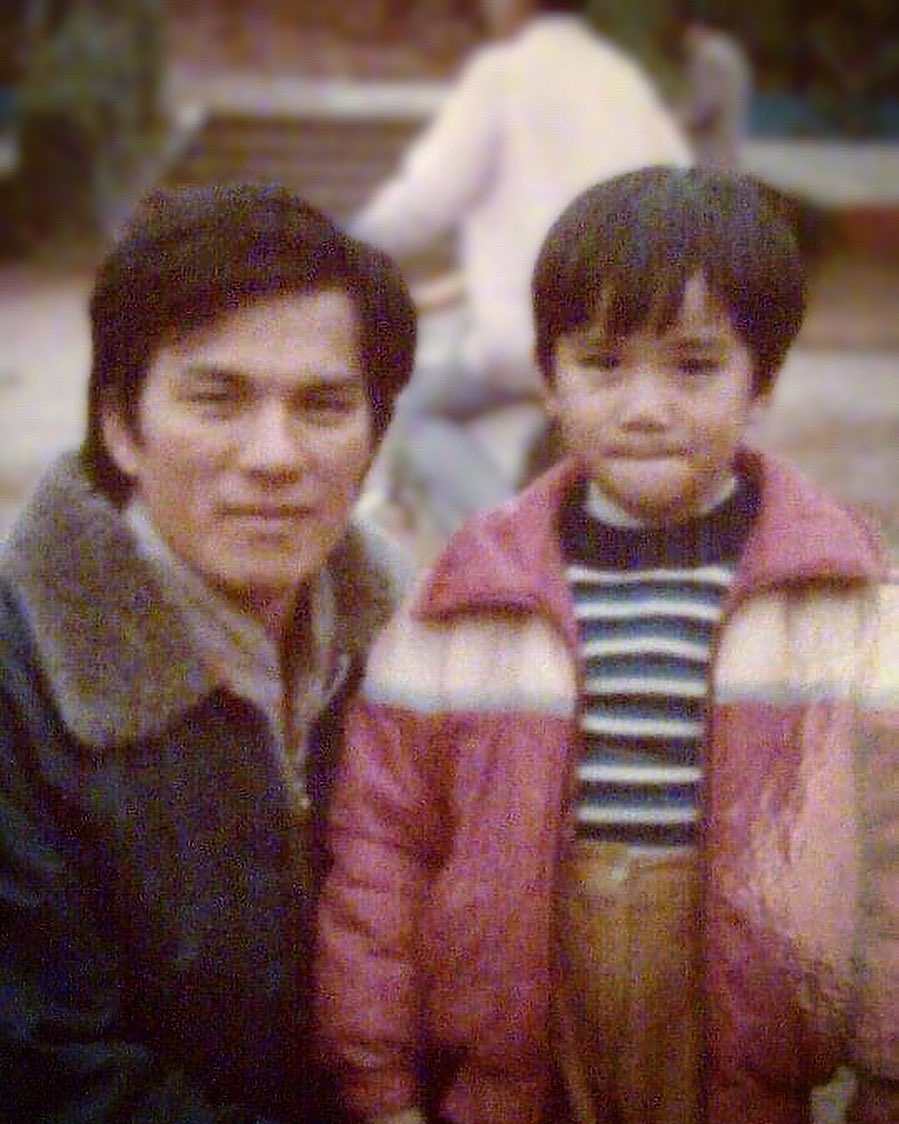
「我一直有感覺到我父親很愛我們,一直有這種感受。」記憶中的父親,永遠面帶笑容,永遠不吝嗇表達愛。然而成長過程失去父親的引導,始終是癒合不了的傷口,所以在每一部創作裡,他都藏進了對父親的嚮往,這份嚮往,也直接地影響他的人生觀,「對家庭,我很憧憬,我希望我可以組成一個完整的家庭,並且給我孩子滿滿的父愛。」
2018年和魯凱族的盧悅婷結婚,2020年迎來第一個孩子,馬志翔在社群寫下:「我們給你取叫Boya,是承自你已逝爺爺的名,爸爸媽媽愛你,你也要不吝嗇將你的愛與溫暖分享給別人,希望你一生健康、平安,腳踏實地走在光明路上,即使崎嶇難行,不怕,腳底的傷疤會讓你成為更好的人。」這是馬志翔對兒子深深的期盼,也是叮囑,是引導,像是以此彌補了自己成長路上的缺憾,把雙份的父愛都給了兒子。


聊到這裡,他忽然想起結婚前母親拿給他的一本日記,是父親的日記,只有短短二、三十篇,寫於他在台北唸書時,母親離開父親、北上陪伴他的一小段時間,「裡面有三個重點:第一個是我父親對我母親滿滿的思念,再來一個是對我跟我哥哥重重的期盼,第三個是我父親的禱告,禱告希望他的孩子可以長成什麼樣子。」馬志翔無比驚訝,彷彿父親預知了什麼,那些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挫折,無解的問題,全都在那本日記裡。
他笑說,日記翻到最後一頁的背面,母親還給父親回了信,「我媽媽回信大概是:你平常都會說愛我,我都覺得很噁心,可是現在當我想要對你說我愛你的時候,你卻不在了。字沒寫完,但是真的像電影情節一樣,我看到淚痕在那個日記上!」
這幾年他確實開始思考,該用什麼角度去講這個故事,可又不想挖得太深。自《KANO》之後,馬志翔已十年沒有創作劇情長片,雖然口袋裡早已完成五個劇本可以拍,但實際執行又是另一回事。2023年,他以《樂之茉》參與金馬創投,是十幾年前就已發想的本,故事透過孩子的視角描述原住民神話,「現在五個本,這個是我第一個想拍的,因為我的孩子,所以我想先處理。」


一聊到小孩,馬志翔有藏不住的喜悅,還不吝嗇地秀出手機背景圖:最親愛的老婆和兒子。然而新生帶來喜悅,亦有擔憂,怕兒子如果生活在台北,對於自身原住民身份會越來越模糊,因缺少環境共感,難以產生情感連結,所以他已和家人搬回花蓮兩年,「讓他在這塊土地上有很多家人陪伴,有很多原住民身份的認同,這種東西才會產生自信。我不希望孩子像我以前沒有自信。」他持續努力說著原住民的故事,說給孩子聽,也說給每一個台灣人聽。
採訪撰文/蔡若君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余香凝(左)陷「婚禮」危機-110x8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