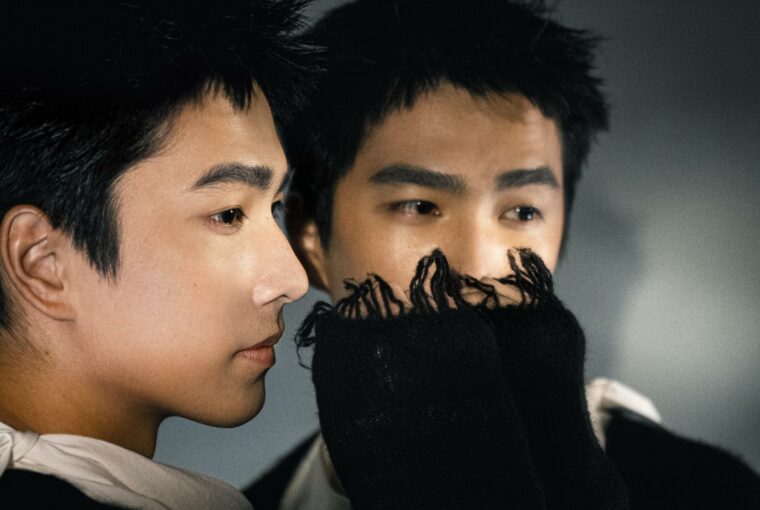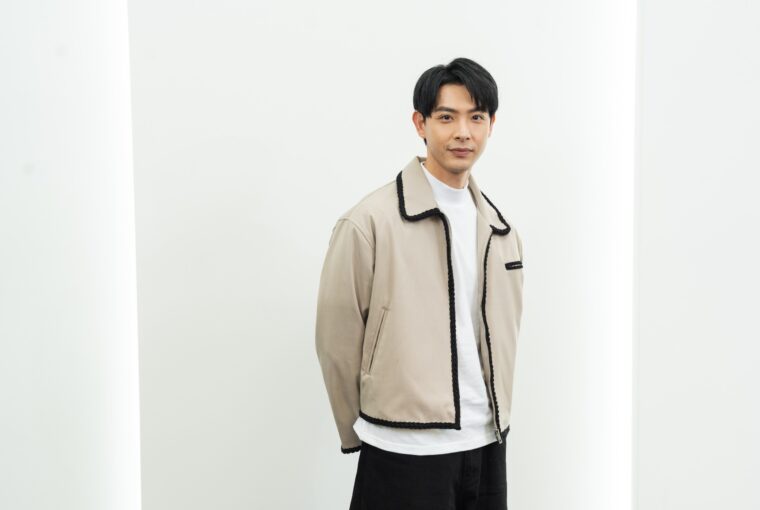《我們六個》開拍之前,劇組安排了游珈瑄和劇中角色原型林秋伶本人,進行了一場線上分享。她一直記得秋伶和她說的那句:「我覺得爸爸是很愛我們的。」這句話讓游珈瑄心碎,正在描述那場訪談的此時此刻,她也泛著淚光,「她一直都把爸爸對他們的付出跟愛放在心上,就算發生了那些事情,她還是可以很理直氣壯、超級真心地告訴我們,她覺得爸爸是很愛他們的。她說爸爸真的很愛他們的時候,我懷疑我聽錯誒!要不是她這麼說,我會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她到底在撐什麼。」


秋伶到底在撐什麼?流落街頭、背負家計、放棄學業和夢想、面對官司的殘酷,任何一項落在身上都如千斤之重,何況秋伶同時承受了每一項。游珈瑄坦言,起初她完全無法理解,那宛如古早味言情小說女主般的堅韌形象,是真的?「她要做任何不負責任的決定是不會有人怪她的,因為這對任何人來說真的都太難了。可她卻選擇撐在那邊,我不能理解。」直到和秋伶本人有了對談,看了秋伶和編劇對於家庭鉅細彌遺的訪談書寫,才恍然一切都太真了。
原來都是因為愛啊。
排行老二不知怎麼演大姐,家人眼中的她既白目又很廢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Reels,就是老大要出門的時候,爸媽會說:『不要玩太晚回家!』老三要出門的時候,爸媽就會說:『記得回來吃飯喔~』然後老二就是:『你怎麼在家?』」游珈瑄就是那個「你怎麼在家」的老二。
整天神遊,飄來飄去不知道又飄去哪,上有姊姊,下有弟弟,老二游珈瑄可一點都不像《我們六個》裡的大姊林秋伶,「我弟和我,都是我姊在照顧。」所以,要作為「大姊」照顧大家這件事,她一度不知道該怎麼演。於是還跑去請教了自己高中到大學的好朋友,好朋友作為老大,有三個弟妹,在群體裡總是習慣照顧著所有人,「他就開始講一些我平常完全不在乎的事情,比如小弟鬧脾氣就要趕快去安撫,不然最後爸媽就會罵他。要是我就會Don’t care~」


游珈瑄毫不留情地自我吐槽,在家人眼中和朋友眼中的她,是個總在做些讓人翻白眼事情的「白目」,不只白目,還(在家)很廢,「我姊看到大家的追劇評論(誇獎游珈瑄演的林秋伶),她都會不以為意。她朋友就會問:『妳妹平常都這麼能幹嗎?』她就想這個人什麼都不會做!」吐槽游珈瑄的還有自家親媽。劇中,林秋伶因為爸爸多日沒回家、衣服堆積如山,所以嘗試操作先前從不需要她來操作的洗衣機。媽媽看到那一幕,直接脫口而出:「她會用嗎?」那個她,指的當然不是戲裡的林秋伶,而是戲外的游珈瑄。「我會洗衣服的!」游珈瑄不服氣補充。


家有非典型母女,媽媽像姊姊、姊姊更像媽媽
在《我們六個》中,性格堅韌的林秋伶,在家逢巨變後姊代母職。也為保護柔弱的母親,憤而起身對抗父親,這是游珈瑄最感共情的部分,也是她認為最難演的。比如要對母親說出「妳不是都很清楚嗎?跟他離婚好不好」這句台詞,就讓她備感沉重,「我會覺得這句話像在教媽媽做事,怕講這麼平輩的話,不像個女兒,在那個年代好像會很奇怪。」
2021年,游珈瑄以短片《家庭式》奪得迷你劇集(電視電影)最具潛力新人獎,於頒獎台上說道:「我們22歲完成了一個極盡一切努力的作品,我要把這個獎獻給我媽媽,她在她22歲,女性最精華最寶貴的時刻,選擇生下我,我要把這個最非凡的一個獎項獻給媽媽⋯⋯」所以她說,和媽媽的親密感,既像母女,又像姊妹,反倒是姊姊更像個「媽媽」,弟弟與她皆屬姊姊管轄。


游珈瑄分享,上幼稚園以前經常被媽媽帶在身邊,一起到市場工作,整個市場就是她的遊樂場,而這也讓她提早見識了走跳社會的各種不易,「她常讓我覺得很像是朋友,看到她常把自己放在很危險的處境裡面,然後她會接受我給她出的建議。我在讀書之後,才開始覺得原來爸媽是給建議的人,可是在我的成長過程裡是反過來。所以我會覺得我們很平輩,不是典型的母女。」姊姊像媽媽,媽媽像姊姊。游珈瑄現實生活中和媽媽、姊姊的相處模式,也如戲劇裡般交替了位置。
賭博阿嬤是《家庭式》原型,家中曾發生《我們六個》討債情節
自編自導的作品《家庭式》,是游珈瑄於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的畢業製作。而走上演員這條路,就是從找不到演員、只好自己「下海」的這部短片開始。游珈瑄坦言,本來拍完後,甚至沒打算繼續做影視相關工作,更不要說「想成為演員」。然而,因緣際會進入一家編劇公司上班,寫著她喜歡並痛苦著的文字,更出乎她意料地,憑藉《家庭式》入圍第22屆台北電影獎最佳新演員、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短片,還拿下了一座金鐘。一切都像是無可奈何的順其自然。
和許多創作者一樣,第一支作品多從自身取材。游珈瑄在《家庭式》裡那個開賭場的阿嬤的原型,就是她自己的阿嬤。她說那是一種豁出去的感覺,「那時候覺得,之後我可能不會再做跟電影有關的事了,所以才敢把這個秘密拿出來。」挖得這麼深可曾後悔?「我不知道誒。但我覺得,把《家庭式》的故事說出來,以及拍了《我們六個》,這兩件事在我們家好像都帶來一些改變。」


阿嬤賭博、討債人追到家,對家裡的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堪回首的痛苦回憶,如佛地魔般的禁語、被關進房間的大象,是個難以言說的禁忌,「《家庭式》有我自己對這個家的詮釋,他們看了之後才知道,原來我是這樣想的,就滿赤裸地,然後大家就開始把這件事當成是一個可以討論的事,不然以前它有點像是禁忌,大家都不想要聊。」游珈瑄還邀請阿嬤去看片,阿嬤看完只說:「我們賭場是給人家喝咖啡,不是喝茶啦!」一句無關緊要的感想,禁忌不再是禁忌。
《我們六個》裡的討債情節,也曾在游珈瑄家裡上演,「我舅舅就說,以前討債的時候,阿嬤是會先落跑的!所以她沒有看過討債,現在剛好讓她看一下!」游珈瑄像說笑話似地開懷大笑說著,可背後依然藏著哀傷,「最近會收到一些人的心得,我才覺得這好像是我們爸媽的那一整個時代,好多人都經歷過家長不是那麼『家長』,很多人也是那麼辛苦努力長大,這對我來說滿震撼的。」


演員像是集體創作,編劇是自己跟故事大眼瞪小眼
游珈瑄的演藝經歷介紹,通常是這樣開始的:2020年以短片《家庭式》出道,至今五年⋯⋯,「我每次聽到『出道』就會覺得很奇怪,這個詞一直讓我覺得,有點像歌手出了一張專輯。」她沒有那一種時刻:這是一個出道了!有戲來找,就去演,演的時候知道自己是名演員,可又不只是演員,她還持續在寫,時不時有劇本案子合作就接,像接任務般,在演員和編劇兩項工作間來回跳躍,跳出自己的節奏,都是創作的磨練,「這兩件事對我來說滿像的,只是演員會有各部門一起幫角色說話,比較像集體創作;編劇就只有你跟故事大眼瞪小眼,會覺得比較孤單。」


她不像其他新人演員那般,懷踹演員夢多年,或有著強烈企圖心,想要奮力一搏演出所謂的「成績」,「好像以前大家會覺得,一個職業要做一輩子。可是我覺得現在大部分的人,同時間可以做很多事情。」哪怕接不到戲就繼續編劇也無所謂?游珈瑄的眼神透露著猶疑,「現在很明確會繼續做演員。只是一個拍攝或一個案子快要結束的時候,會有瀕臨失業的焦慮,但每次好像都會絕處逢生。」游珈瑄選的不是一種職業,而是生活,每逢柳暗,又見花明。她等著下一個如《我們六個》般的又一村。
採訪撰文/蔡若君
責任編輯/許容榕
核稿編輯/李羏圖片/游珈瑄IG、我們六個FB


與桂綸鎂飾演的夫妻,在長年壓抑與失衡中逐漸崩解-110x85.jpg)




-1-760x510.jpg)